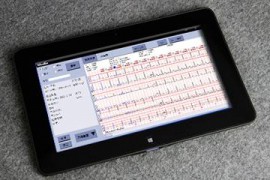ECG,心电图机
传统心电图发明至今已百年余,可谓“既熟悉又陌生”。前者是指简便、广为普及,是在一维线性表达基础上建立起的一套理论体系,如: Einthoven-Goldberge-Wilson导联体系、容积导体、电偶学说、细胞跨膜电位、合体细胞、单个心肌细胞的跨膜电位变化视同整体心肌的动作电位、心肌电活动紊乱是以心肌细胞性质改变为基础等。当前,临床上又提倡12导联ECG的同步描记,认为导联数目越多、指标越多、准确性就越高。
“陌生”是基于对ECG所形成的机理、作用、意义、利弊以及今后的发展并没有被深刻的认识。没有认识到ECG的优势只在于一维线性描记,即对时间域的表达十分突出,主要用于长时间连续描记多周期的心跳,观察其频率和节律。通过分析各波形先后出现的时间,反推心脏激动过程中传导时序的关系,实质上还是侧重于对传导束的研究。相较之下仍然不及创伤性电生理检查术对传导路途中各“站、点”的描记更为直接。
人们对ECG的观察指标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: 时间、振幅和形态。由于各个导联轴线是对平面VCG环体从有限几个角度的再次“切割”,所以也只能反映出在该导联轴线上相对应的正负两点间的时间、振幅(电位差值)和波形变化。由此,从各导联轴上制定出的常见检测指标亦多达上百种,其中绝大多数是多导联重复性的指标,不仅十分繁琐,而且心房、心室肌除/复极时,唯一真正准确的时间和振幅是多少并不知道; 各波形的形态变异也难以解释清楚。
如: P波时间,在12导ECG中人为地将其范围扩大到0~0.11; P波振幅范围在0~0.25mV; P波形态的改变更是千变万化,让人难以掌握其规律,这当中包括了人体差异、人为因素、电极位置、生理性干扰、病理性异常、传导束的起搏传导、心肌的反应扩布(心肌各向异性)、心室肌负极肌性传导束的假说、环体的转向、形态、方位、时间、振幅、角度,神经体液等因素的影响。表现为单/双峰或双向,双向中又分出先正后负及先负后正等。再具体到P、QRS、T、U波形的大小、宽窄、重叠、融合、粗钝和切迹等等,致使其真正的形成机理、唯一而准确的检测指标和各波形内在的特征等,在一维线性的平台中是根本不可能说情楚的。
U波: 至今难以深入研究。
Ta向量: 从ECG中看不出。
ST向量: 机理、方向、夹角、相互关系的探讨难以再深入。
T波: 代表心室肌的复极过程,是主动转运机制,理论上应该更能说明心肌病/生理变化的早期状况,心电学改变早于解剖形态学的改变也早已得到证实,这对于临床早期诊断、预防和治疗原本十分有益,但受到一维表达的局限性致使许多影响因素难以进一步被排除,特殊性体现不出来,结果只能认为特异性不高临床意义不大。
方位: 是通过额面的六轴系统定位上下左右,但因轴间夹角均为30°,使得未被偷摄(切割)到的总面积偏大,盲区增大,仅仅是粗略定位; 通过横面定前后,由于胸前导联(V1~V6)多数放置在胸阔的左心前区,并投射到胸阔的右后区域(负值),覆盖面积仅达230°、盲区面积为130°。有人认为通过ECG的上下、左右、前后描记就能表达出空间方位,此说法不准确,因为不同时具备长、宽、高的描记就不构成立体,即使轴线再多仍为线性。理念上要么纯属线性,要么就靠在两次投影上,后者应该更科学更系统,因为心脏是立体结构,业内人士也公认ECG由VCG所产生,假如否认了VCG那么ECG又从何谈起呢?何况立体的心电环体实质上是由传导束和心肌电/化学扩布所构成,二者的理化性质截然不相同,绝非传导束与合体细胞的简单关系。临床上曾采用的两条电极导联体系被认为对所谓“右室心梗”的诊断有意义,实际上这只是将探查电极放置在胸廓右前区的“盲区”而已; 采用几十根电极放置方法,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缩小了“盲区”范围,但是,二者都受到错误的“心电位”概念的影响,即某个导联电极面向某处心肌并反应出该局部心肌的心电改变。同时,众多的导联轴线并不能反映出心肌电/化学扩布的特点(心肌各向异性)。
平均心电轴: 是用来检测振幅的角度和长度,采用Ⅰ、Ⅲ导联的R波面积或振幅的差值来说明左偏或右偏,也是利用了心电向量原理作出大致上的简单量化,并不精确。
Q-T间期离散度: 作为个体观察在同一导联上做比较,原理上能说通。但作为群体观察,最大/最小比值不仅因人而异变化大,而且两个导联的“视角”本身就不全面不准确,且数值可变性大,标准不严谨,所以根本就不具备可比性。然而,同一导联上的细微变化通过目测观察其准确性又如何呢?在不清楚挫折、切迹、钝挫等现象产生的机理是什么,何为生理性及/或病理性,就笼统地做出高频处理,意义何在呢?
总之,一维空间性质(平台),决定了ECG在时间域(时序性)表达的优越性,可以观察连续心跳的频率和节律,简单、便于普及。但是,由ECG描记出每个心跳周期的时间、振幅,尤其形态是不可能比平面和立体空间中所能够体现出那么全面、直观、细致和准确。相反,导联越多,时间、振幅和形态的变化越多,指标越繁复,假说越多,反而越不准确。